|
为了这一针—乙型脑炎和出血热研究的往事回忆
一、一次惊心动魄的现场试验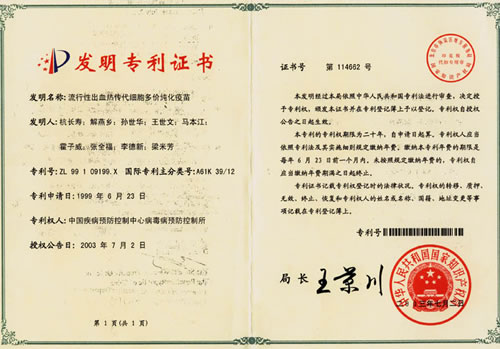
在陈伯权教授等人的努力下,乙型脑炎减毒活疫苗获得突破性进展。他与我同时进行了试用,而后又扩大至所内的同事共27人,都是非常安全的。但是在人们心中,特别是在上级领导心中对这种疫苗的安全性还有疑虑的,因为它毕竟是从强毒株衍化而来的,它对儿童是否也是安全的呢?当时还没有很有说服力的证据。在大家讨论时,黄祯祥教授提出很好的建议,他说脑炎在马中的发病率较人要高10倍,这说明至少马比人对脑炎更敏感,如果我们用马(驹)做一个疫苗脑内注射试验,若马不得病或死亡,就能很好证明它对儿童的安全性。我认为他的想法很好,如果我们把人用疫苗打入马驹脑内而不引起疾病或死亡,这是一个有关安全性方面很有说服力的“双保险”证据,说明疫苗病毒免疫儿童一旦入脑也不会引起严重问题,产生疾病。
这个试验由我具体筹划实施。起初向张家口联系可供试验的马匹,最好有外伤残疾的马我们可做一个预试验,如果成功也可说明问题,而花的经费不会太多。因为我们与张家口畜牧水产局的关系甚笃,相信他们一定能全力帮助,不会有任何问题。结果真的在张北庙坛牧场选择了两匹才6个月的马驹和距100公里左右的一个军马场选择了两匹退役马。后者虽不合我们原先所要求的试验对象,但它们分别代表年轻者和年老者对乙脑疫苗的敏感性,加之他们不要我们付钱,故可一试。第二个问题是怎么做这样的试验呢?如何把疫苗打入马脑内呢?原脑炎室的同志如注射小白鼠或乳鼠脑内,闭着眼睛都行,而对这样大个和那么坚硬的马脑怎做呢?它的解剖部位又是怎样的呢?我带了肖培英先后走访了图书馆、兽医院了解马的脑部结构,在询问脑部手术的经验时,接待的兽医生说,凡遇动物脑部疾病时就放弃了。不得已我们只得拜访人医,在中国的一所顶级医院里,我们受到神经外科主任的接待,他帮助我克服了很多疑虑,包括如何用颅钻打开脑颅等问题。但是当我问他是否可借一个富余的颅钻供我们一使时,他就说我们只有这一个。后来我们去了宣武医院,在那里我们真的大开了眼界,该院科技处听到我们的来意后,就热情地说今天正好有两台开颅手术,马上叫护士把我们带到手术室,穿上隔离服直接进到里面观看。我是医学院毕业的都知道,除了做助手,很难与手术的主刀面对面。他们这样信任我们真让人感动。主刀是1967年毕业的大夫,而助手是1972年刚毕业不久。他们胆大心细,做的非常利索,而且不时说一些笑话,表明他们心里一点不紧张。最让人感慨的是他们所使用的颅钻产自瑞士完全是自动化的,它的设计非常巧妙:整个颅钻分两截,上截转动带动下截及钻头的转动,但当钻头碰到软区或软组织,下截就即刻与上截分离,虽上截依然转动,而下截仃止一点不动。他们在颅骨上打四个孔仅需1~2分钟,不怕钻头插入脑内。然后又用钢丝锯把颅骨锯开,去除脑部病灶。看了这手术后我感到心里有了底。后来又打听到张家口兽医院有开颅用的圆锯(说明动物脑部有病也不是都放弃的),它虽比不上自动化的那种好,但比顶级医院那种要好用得多,安全得多,因为它在颅骨上是平衡转动。那天正是尼克松来中国访问,我与黄祯祥教授一起坐火车去张家口,在张家口兽医院邀请了一位会做脑颅手术的兽医师,先后到两处进行马脑内疫苗注射试验。结果是军马场的两匹退役马中一匹因注射53株疫苗而死亡,另一匹注射28株疫苗则无事;但在庙坛牧场则却好相反,注射28株疫苗的马驹有发烧和一些体征,而注射53株疫苗的无任何反应。出现这样矛盾的情况,加之使用的动物不是正常马匹,故很难正式去说明问题,所以与黄教授讨论下决心使用健康的正常马匹。要使用正常马匹做试验谈何容易,首先要征得领导同意与批准,为此当时的董秉琨书记专门召开了党委会,由我向他们报告要进行这个实验的目的意义、方法及需要的经费开支和希望领导的支持等,而后董书记征求每个成员的意见,大家都非常赞同,最后董书记说,他也支持并告办公室马上打报告给院里征得院里同意。其次是从哪里去获得马匹呢?当时,在农业上蓄力非常紧缺,特别是北方人们都依靠马驴作为最主要的运力;在军队“部队要实现驴马化”,对驴马十分的看重。好在人们对科学研究的支持是无私的,一旦他们认识到你所进行的研究对我国的经济、国防建设有实际意义,一般他们都会全力支持和帮助。我跑到总后卫生部而后又转到军马部商量他们所属军马场中马匹做试验的问题,意向不到的是他们马上与所属一个军马局联系,对方回应派人面谈。我和杨崇泰同志前去该局,那是在内蒙古白银库伦,离锡林浩特南约100多公里,傍边有一个非常大的白银库伦淡水湖,据说有很多鱼,特别是鲫鱼。该局管辖的白银库伦军马场也在同地。经过几天的奔波与该局谈妥有关用军马做试验的一切问题,记得那天离开时天正下着雪,大家都感到很惊奇,因为到6月已不到一周时间了。
6月下旬一天,我们一行5人(黄祯祥、金恩源、林海祥、周鑫海和我)由所里出车直奔白银库仑军马场。临走时我特意去党委向党委一班人告别,他们正好开会,董秉琨书记说“我们停一下,去送送他们”,党委共10余个同志即刻来到大门口列队与我们一一握手告别。党委的这一主动,让我们一行非常感动,大家都决心把这个实验做好。在实验进行过程中董书记还专程来试验现场看望,使大家的心始终是热切的。
来到军马场,准备从一个一岁龄的蒙古马马群中挑选20头做试验,场里又给配备了4个马倌,他们都是从沈阳来的知识青年,对各种马的性能都很熟知,由他们负责对这马的饲养和管理,他们工作很认真对我们很热情因而与我们关系很好。
在马脑内疫苗注射试验的那天,我们起得很早,早上4点开始工作。我们在该马场一个诊室和化验室内,黄和林在化验室中负责将疫苗抽入注射器针管内待用;金与一个兽医准备测量试验马的体温及注射疫苗后给马打抗菌素;周与马倌,还有很多帮忙的人去马厩捕捉马匹,由我与另一兽医分别主刀和助手。捕捉到马匹是试验成功的关键一步,逮马非常惊险,像是马戏团演出惊险节目一样:一个骑士骑在一匹训练有素马背上,他右手上拿着一条竹竿,竹竿头上拴上一条麻绳一头,并与竹竿间留出约一米左右直径的套子,而另一头简单地盘在竹竿上几圈后由骑士用右手握住。只要骑士用竹竿一指那匹马,骑马就心领神会追赶它,靠近时骑士就用竹竿上的套子轻轻一撒,套住那马的头,骑马会立即停下来(四肢一动不动),这时骑士用双手旋转竹竿使套子的直径缩小,下面同伴沿竹竿接近被套马,揪住耳朵换上笼头和缰绳,就算完事。把逮住马拉到诊室和化验室是关键的第二步,一个自由惯了的马驹,现在套上笼头和缰绳让牠跟人走没有那么便宜的事,需要两个人在头里牵,几个人在后头赶,而进入房间内就更不易了,只能强拉硬推,人室内的马驹,上串下跳驾驳不住,几乎所有的门窗玻璃全碎了!真是惊心动魄,太惊险了,我们一生中没有经历过这样实验。好在我们人多,有的揪耳朵使其老实,有的用绳子拉四条腿,有的用手推其上身,一下子把牠推倒在地,并立即把其保定。余下就是我与兽医做开颅手术了:切开头皮,暴露头骨,用颅钻钻出一公分左右的孔,打入1毫升疫苗,然后缝合皮肤和简单包扎,整个过程大约需一个小时。我们采用随机分组的方法,即一匹注射28株疫苗,下一匹就注射53株疫苗。中午吃中饭才半个小时,到食堂还需走10分钟,每人一大碗红烧鲫鱼真是够吃的,要在北京至少也需花一个小时,故只能草草了事,感到很可惜,因为当时全国副食紧缺,哪里看到过这样鲜美的鲫鱼哩!我们一直干到4点钟共才注射了10匹马,即5匹注射28株疫苗,5匹注射了53株疫苗。大家已感到精疲力尽,好象经历了一场严酷的战争,需要休整。按黄教授意见,这样也可以了,因为这类病毒对马非常敏感,结果可以说明问题。故将另外10匹作为阴性对照。
此后,我们一行每天给试验马(包括对照)量体温并观察各种反应。我们还参加马场的许多活动,如修马路和打草等,前者还得到过马场的表扬。我们也搞一些文体活动,如骑马、打乒乓球等。打乒乓球我可能是倒数第一、二,但是骑马我肯定是第一。
我们在那里呆了一个月左右,结果是非常理想的,没有发生明显的疾病。仅其中注射28株疫苗的10号马,有几天发烧;注射53株疫苗的13号马也有一些烧,后因后腿外伤被狼吃掉。总之,我们的实验是非常成功的,说明疫苗是非常安全的,即使注射105.5TCID50/Ml
病毒进脑也不会引起脑炎。虽然在处理马匹遇到一些问题,让周鑫海同志在那里呆了很长一段时间,但是最后处理还是圆满的,全部转卖给北京卢沟桥公社作为农用马,我们最终没有花太多的钱。但通过这个实验,对于疫苗安全性我们有了更多的把握,上级就批准我们扩大疫苗在张家口的人体试验,由陈伯权教授带队在那里共接种了1400人,的确是安全有效的。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
|